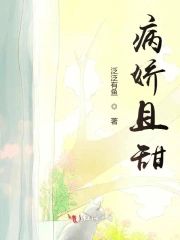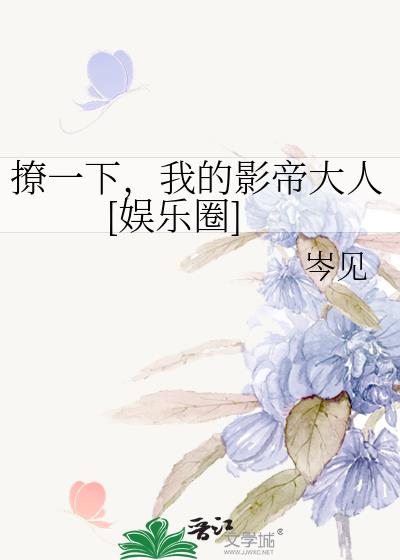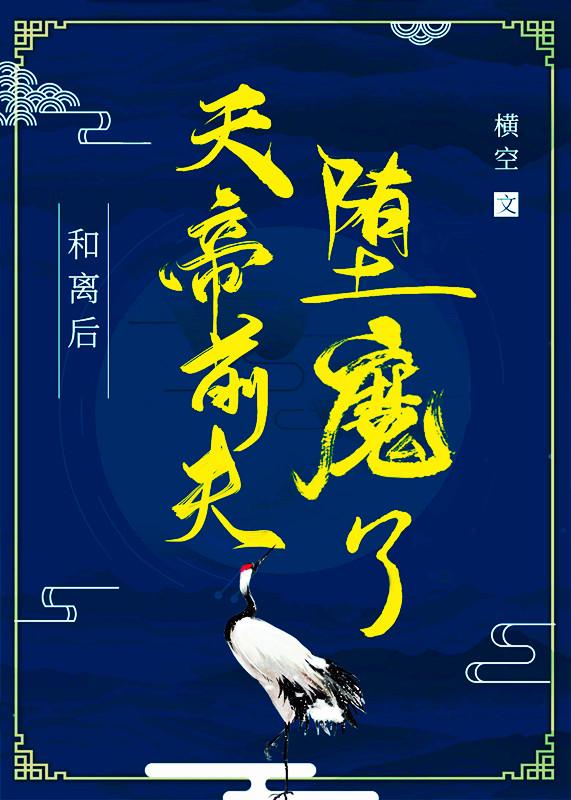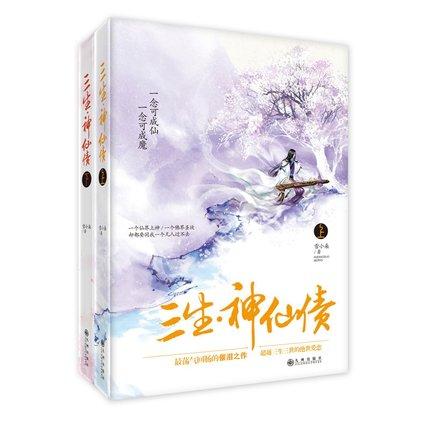多次瞬移之後,沈辭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了,渾身上下就沒一塊好肉,全是血淋淋的。
好不容易瞬移到了一個都是人族生活的島嶼,沈辭就再也支撐不住,昏死在海灘上。
這個島嶼就是姜米島!
海灘對于島民們來說,是最危險的地方,從小就會教育自家的孩子,不準自己跑去海灘玩,會被海獸吃了的!
姜糖的“失蹤”就是姜米島上一個慘痛的教訓。
小時候的姜糖不懂事,一個人跑到了海灘上玩,被海獸也吃了,這海獸吃完了姜糖還嫌不飽,又吃了問訊趕來的姜同一條腿!
姜同就這樣沒了一條腿,還沒了最珍愛的女兒。
妻子劉氏目睹了這一切直接吓暈了過去,反而免遭了被吃掉的厄運,但是,醒來後的劉氏悔不當初,恨不能用自己去換女兒,生生哭瞎了一雙眼睛。
好好的一個家就這樣變得愁雲慘談,凄苦不堪。
姜米島的海灘邊更沒有人敢去了。
只有不甘心的劉氏,睜着一雙看不清的眼睛,懷着說不清的可憐希望,還是會常來到海灘邊轉轉,像是她的女兒還能回來似的。
三年前,就是劉氏在海灘上發現了沈辭,把一身是血的沈辭撿回了家。
誰也不知道,她一個體弱多病,眼睛也看不清的瞎婦人哪來的這麽大力氣!
姜同回到家裏的時候,看見妻子又哭又笑地跟他說“同哥,咱們家糖糖回來了!”
聽見這話,昂藏七尺的大漢眼淚“唰”一下就滾出來了。
那個時候,兩口子就決定了,要留下這個孩子,這就是他們家糖糖!
沈辭雖然還沒力氣醒來,但是依然将身邊的動靜看了清楚。
因為她的突然出現,整個姜米島的島民都感到了“震蕩”!
在位于迷疊海深處的姜米島,海灘上出現什麽恐怖的海獸都是正常的,唯有這樣漂上來一個人,才是最不正常的!
迷疊海上最值錢的是能修煉的人,是海修,可是最不值錢、最卑賤的,也是人!
誰知道這個滿身滿臉都是血的女娃子到底是個什麽?
整個島上也沒有一個修士!
沒有一頭高等海獸!
姜米島的特殊情況,與姜平有關。
其他住着人族的島嶼,不是有海修當島主,就是有高等海獸當島主,把持,或者說看守着島嶼上的人族。
唯有姜米島,島主姜葉就是個普通的女人。
沒有人能看出沈辭的深淺,誰也不知道她其實是個化神期的修士!
但是愚昧和無知,很多時候,也是能傷人致命的利劍!
沈辭聽到島民們商量了許多處置她的方法。
有說要把她扔回海裏的,也有說直接把她處死了的,還有說要報告這附近的高等海獸虎鯊将軍的,最平和的也就是把她扔回沙灘上,讓她自生自滅……
每一種方法,在這個她最虛弱無力的時候,都可能讓她死無葬身之地!
聽到島民們的商議時,沈辭差點沒氣得吐血!
同時,她也為這群在海上讨生活,完全失去了脊梁的人感到悲哀,更為自己感到悲哀!
這群島民已經完全失去了人族的脊梁,他們已經在海族長久的統治下習慣了卑躬屈膝,奴顏求生。
對于一個重傷瀕死的同族,他們提不起一絲半點的同情,他們責怪劉氏,認為是劉氏将這個麻煩帶回了島,唯恐這個半死不活的人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災難!
沈辭突然覺得好迷茫,她千辛萬苦地來到迷疊海當間諜,雖然有着尋找石胎的目的,但是,能為人族傳遞消息,做一些事,她覺得很有意義,很有價值。
當初,在碧水宮中看到,淪為奴隸卻仍懷着不屈之志的錦悅等人,沈辭心中萬分敬佩,也覺得自己和碧若這些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!
因為在迷疊海中還有許多人,像錦悅等人一樣,在迷疊海中經受着苦難,希冀着同族的解救。
沈辭覺得自己一個小小的間諜,雖然影響不了人族海族的大局,但能盡一份綿薄之力,也不枉為人一場。
可是,我欲救人,人卻欲殺我?
在完全不知沈辭的情況時,出于趨利避害的本能,人們最和善的做法竟然也不過是讓她自生自滅,放任她死去!
而其他的每一種方法都會讓她死得更快!
沈辭聽到這裏的時候,心中真是戾氣深重,可是她什麽也做不了,她現在沒有再動一動的餘力!
她第一次冒出一個可怕的念頭我與你們井水不犯河水,你們卻想要我去死?那我即使拼着受更重的傷,即使境界跌落,我也要報仇!夷平這座島!夷平這島上所有醜惡的人!
當她冒出這個想法的時候,在軀體、元嬰重塑之時都沒有動靜的地心之火,突然被釋放了出來!
熊熊的火焰所有人都看不見,就在沈辭自己體內,元嬰上烈烈燃燒着,讓她的軀體和元嬰真正如鳳凰涅盤一般,浴火重生。
傷口在飛快地愈合修複,但是争執不下的島民們并沒有發現。
不知該說是沈辭的幸運,還是島民們的幸運。
沈辭最後還是被留在了姜米島,因為姜同和劉氏的堅持!
姜同和劉氏那個時候說過的話,沈辭這輩子也不會忘記!
劉氏哭泣着、嘶吼着“你們還是人嗎?她是個人,我知道!她是個活生生的人!她還沒有死,還有的救!”
姜同則說“她就是我的女兒姜糖!是老天可憐我們,才又把她送了回來,我們不能再失去她了!”
也許是劉氏的質問讓島民們僅存的良知動容,也可能是沈辭看起來實在是活不成的樣子。
再加上姜同許下了,會被搬家移到姜米島最邊緣的地方,一旦出事不會牽連族人等等承諾。
最後,在姜同和劉氏的堅持之下,島民們總算松口,“姜糖”被留了下來。
但是,他們一家三口被島民們幾乎完全隔絕了,家家戶戶都刻意不與姜同家來往,對姜糖的來歷也諱莫如深。